一
是暴风雨将来的一个黄昏。
死灰色的天空,涂抹着一堆一缕的太阳的红焰,那刺目的猪肝似的恶毒的颜色,使人看了便有些压迫之感,至少是不舒服。
宙士,神与人的主宰,郁郁的坐在他的宝座上;伏在座下的鸷鹰,时时在昂头四向,仿佛只等待宙士的命令一下,就准备着要飞腾出去,捕捉什么人与物。他手上的雷矢,在炎炎的发着白热以上的火光,照耀得立在他左右的诸神都有些目眩头胀,间或隆隆的发着雷声,其声闷而不扬,正足以表示其主人翁的蓄怒未发的心境。
一切都是沉闷,郁怒。
火山口将爆裂的一刹那,暴风雨将降临的前一刻。
等候着!未前有的沉默与等候!
神们都紧皱着双眉,装着和宙士同忧共苦。连娇媚的爱神爱孚洛特蒂也乔作颦态,智慧神雅西娜的无变化的淡靑色的脸上却若在深思。宙士不时的象发疑问似的望着她。她并不变动她的深思的姿态,也一声儿不响,活象一尊无感情无知覚的墓前的翁仲,永远沉默的对着西坠的夕阳。天上的鉄匠海泛斯托士,那位柔心肠的残疾者,心里正忐忑不宁,不忍看这幕活剧的进行,但又不敢离开,只能痛苦的等待着。
权威与势力,那两位助桀为虐的神的奴,一对玩鉄的铸象似的紧密的站在宙士宝座的左与右;他们俩喜悦的跃跃欲试其恶辣的手腕;他们知道这场面上免不了他们俩的上演。他们握紧了有力的鉄似的双拳在等待着。
一切都是沉闷,郁怒。
等候着!未前有的沉默与等候!
二
神的厅上开始骚动起来,窃窃的微语。神们都转脸向外望。宙士抖擞着威风,更庄严的正坐着,暗地里在寻思着怎样开始发泄他的久已不能忍耐的闷怒。权威与势力活动了他们的紧握着鉄似的双拳一下。座下的神鹰拍拍它的双翼。
远远的有两个黑点,在飞着似的浮动着。
这两个黑点,近,更近,正向神的宝座前面来。
是他们所期待的人物!
前面执着蛇杖的是神的使者合尔米士,后面跟着他而来的,啊,便是那位叛逆的取火者柏洛米修士。
神的厅上转又沉默下来,沉默得连一移足,一伸手仿佛都会有声响发出。
“别来无恙,”那位叛逆的柏洛米修士的丰姿并没有什么变动;山峰似的躯干,忠恳而有神威的双眼,表现着坚定的意志的带着浓髭的嘴唇,鬓边的斑白的头发,因思虑而微秃的头颅,以及那双多才多艺的巨手,全都不曾发生变化。
一见到他,期待着壮烈的,残虐的表演的诸神们反都有些茫然自失;一缕“反省”与“同情”的游丝似幻成千千万万的化身,各紧粘着诸神们的心头,摆脱不开。
未之前有的凄淸的空气,弥漫了神的大厅。
神的使者合尔米士首先打破了这场淸寂,循例的交差似的说道:
“父宙士,您命我去呼唤前来的柏洛米修士,现在已经在您面前了;他一听到您的命令便和我一同动身。”
人与神的主宰宙士似最早便镇摄住他自己的权势和自重,使他立即恢复了他的严肃与残忍。他向侍立的权威和势力瞬了一眼,他们正鉄棒似的笔立着待命;双拳是紧握的伸出,脸部是那么冷酷无表情,这增加了宙士的自覚的威严。
他紧皱着双眉,望着忠厚而多智的柏洛米修士本想立即咆吼的痛骂,却出于他自料以外,发出来的语声是那么无力而和缓。
“啊,你竟又在我的面前出现了,柏洛米修士,我的好朋友——不,现在你已自动的背叛我们而向下等的猥琐的人类那里求同盟,大约已不承认老朋友们了罢?你有理由说明为什么背叛我们而和人类为友吗?”
柏洛米修士山峰似的站在那里,并不恐惧,也不傲慢;他诚恳的微笑着,并不曾说什么。
他该说什么呢?
长久的沉默。
“你,怎么一声不响?”
宙士大声的开始咆吼,但一望着他的那么诚恳忠厚的脸部,又失了发怒的勇气。“你说,尽管无忌惮的说,为什么你要把神们所独有的神秘,火,偸给了人类,使他们如今如此的跋扈?”
想到了偸火的事,宙士不禁气往上冲。火是神们的独得之秘,是神的权威的代表,它只能放光明于神之厅与室,它只能供神作种种的利用的工具。有了这火,便足以夸耀于下等的人类之前,足以为他们永久的主宰而不虞其反抗;人们是在永久的龌龊卑污的生活中度过去的;那么可怜,那么无告,却正是神们所愿的;这样的人类,却恰好是最适宜的神之奴。宙士和诸神们从没有想到这神秘的火会由神之天堂而移殖到人世间,而供猥琐可怜的人类利用的。然而这火却终于不能成为神的独有之秘密!
三
某一个冬夜,宙士带着他的儿子合尔米士踏着琼琚似的白雪而周行于大地上。手掌大小的雪片,在空中飘飞着,北风虎虎的在发威,把地上的一点一滴的水都冻结成冰块。大地上什么都在沉睡,什么都已深深的躲藏着。宙士挺了挺伟健的巨躯,全身充满着热力,雪花到了他身的周围的一丈左右便都已无声的融化而落在地上了;北风对于他也是服从惯了的,只是服服贴贴的悄然从他背后熘过去。
他们俩幽灵似的在雪地上走着,以克服了一切目喜。
他们也许便是此夜的仅有的夜游者。
“啊,”宙士以全肺部的气力叫道,他是高兴着。
大地几乎要迥应着他的游戏喊声而打了一个寒噤。
一个奇迹突然出现了。
远远的,有一星红光在若明若暗的照耀着,映着白雪的大地,似乎格外来得鲜明。
是星光,难道?
铅灰色的天空,重重叠叠的为黑云所笼罩,所包裹,一点蔚蓝色的空隙都没有,哪里会有什么星光穿透重云而出现?
宙士以肘触触跟在他背后的合尔米士,悄声的说道:
“看见了么,你?”
“看见的,”合尔米士微笑的随意答道。他想,也许是娇媚的爱神又在进行什么新的情恋,结婚神正为她执着火把吧?也许是她的儿子,那位淘气的丘比得在闹什么玄虚吧?也许是羊足的萨蒂尔们正在向林中仙女们追逐着吧?也许是酒神狄奥尼修士正率领着他的狂欢的一群在外面浪游吧?
宙士没有他那么轻心快意的疏忽,这位神与人的主宰者,是饱经忧惧与艰苦的,一点点的小事,都足以使他深思远虑的焦念着,何况这不平常的突现的一星红光。
这不平常的一星红光使他有意想以外的严重的打击。
他有一种说不出恐怖的预警。
他一声不响的向那一星红光走去。
啊,突变,啊,太不平常的突变!
走近了,那红光竟不仅是一点星了,一点,两点,三点,……乃至数不淸其点数,此明彼暗的竟似在那里向雪白的大地争妍斗媚,又似乎有意的彼此争向宙士和他的从者投射讥笑的眼风。
连合尔米士也渐渐的感覚到一种不平常的严重的空气的压迫了。
走近了,——最先走近的一星红光,乃是从孤立于雪地上的一间草屋的窗中发出来。
这草屋对于神与人的主宰者宙士异常的生疏,刺目。
他想:“这东西什么时候创建在大地上的呢?”
他们俯下身去,向窗中望着。更严重的一幕景象显呈于眼前。
一盏神们所独有的油灯,放出豆大的火焰,孤独而高傲的投射红光于全屋以及雪地上。
是谁把这盏灯从神之厅堂里移送到这荒原上来呢?
啊,更严重的是,对这盏灯而坐的,并不是什么神或萨蒂尔们或林中仙女们,却是那么猥琐平凡的人类。这些猥琐平凡的人类,当这冬夜向来是深藏在洞窟之中的。
是谁把这盏灯从神之厅堂里偸给了猥琐可怜的神之奴,人类的呢?
宙士不相信他自己的眼。他咬得银牙作响,在发恨。
“非根究出这偸火的人来不成!谁敢大胆的把神的秘密泄露了?只要我能促住这贼啊!……至于这些猥琐的人类,那却容易想法子……”
他在转着恶毒的念头,呆对着窗内的那盏油灯望着。
一阵嬉笑声,打断了他的毒念。
父亲在逗着周岁的孩子玩,对灯映出种种的手势。孩子快乐得“吧,——吧——”的手舞足蹈的大叫着。另一个三岁的孩子伏在他妈的膝盖头,在静静的听她讲故事。
一阵哄堂大笑,不知为了什么。
这笑声如利刃似的刺入宙士的耳中,更增益了宙士的愤怒。
“这些神的奴,他们居然也会满足的笑乐!住神所居的屋!使用着神的灯!而且……满足,快乐!”
妒忌与自己权威的损伤,使得宙士痛苦。他渴想毁灭什么;他要以毁灭来泄愤,来维持他的权威,来证明他的至高无上的能力。
勐一抬头,一阵火光熊熊的高跳起,在五六十步的远近处。
随着听到乒乒乓乓鉄与鉄的相击声。
“这是什么?”他跳起来叫道。
他疑惑自己是仍在天上,正走到鉄匠海泛斯托士工作场,去吩咐他冶铸什么。
那鉄与鉄的相击的弘壮的音乐,有绝大的力最,引诱他向前去。合尔米士默默的随在后边;他也是入了迷阵;却不敢说什么,他明白他父亲,宙士,正蕴蓄着莫名的愤怒。
那是一个市镇的东梢头,向西望去,啊,啊,无穷尽的草屋,无穷尽的火光!
这鉄工场雄健的镇压在市的东梢头,大敞着店门在工作着。火光烘烘的一阵阵的跳起;红热的软鉄,放在砧上,乒乒乓乓的连续的一阵阵的重击,便一阵阵的放射出绚烂的红火花。那气势的弘伟壮丽,只有在海泛斯托士的工场里才可见到。然而如今是在人世间!
宙士和合尔米士隐身在鉄工场一家紧邻的檐下,聚精会神的在望着那些打鉄的工人们。
鉄与鉄的相击声,此鸣彼应的,听来总有五六对工人在鉄砧上工作,但他们只能见到最近的一对。
年轻的一对小伙子,异常结实的身体,虽在冬夜,却敞袒着上身;脸色和上身,鉄般的黑。鉄屑飞溅在他们的手上,臂上,脸上。一个执着火钳,钳着一块红鉄放在砧上。他们抡起庞大的鉄锤来,一上一下的在打,在击。红热的鉄花随了砧锤声而飞溅得很远。两臂的筋肉,一块块的隆起,鉄般的坚强。红光中映见他们的脸部,是那么样的严肃,自尊与自信!这形相是神们所独有的,而今也竟移殖到人世间!
火光映到两三丈外的雪地,鲜红得可爱。
火光半映在宙士的脸部,鉄靑而忧郁。
天上?人间?
一个严重的神国倾危的预警,突现于他的心上。
瞬间的凄惋,忧郁,又为对于自己权威的失坠之损伤所代替。这伤痕,随着砧与锤的一声声的相击而创痛着。而望着那些自重的满足的鉄工们的脸部,又象是一个新的攻击。
他回过脸去。他狼狈到耍塞紧了双耳。
那清朗,满足,快乐的鉄与鉄的相击声,继续的向他进攻,无痕迹的在他心上撕着,咬着,裂着,嚼着。
咬紧了牙,脸色鉄靑而郁闷的转了身,他向天空飞去。
合尔米士机械的跟随着他。
四
这回忆刺痛了宙士的心的疮痕。
“你有什么可辩解的?”
宙士雷似的对柏洛米修士叫道。
“为什么一声不响?”
他为柏洛米修士安详镇定的态度所激怒;血盆似的大口,露出灿灿的白色牙齿,好象要把世界整个吞下去。手紧捏了雷矢一下,便连续的发出隆隆的雷声,震得他自己也耳聋。
权威和势力齐齐的发出一声喊,山崩似的:
“说!”
他们的两对鉄拳同时冲着柏洛米修士的脸上,晃了两晃,腕臂上的靑筋,一根根的暴起。
柔心肠的鉄匠海泛斯托士,打了一个寒噤,回过脸去。
柏洛米修士却安详而镇定的站在那里,山岳似的不动半步。
“为什么不说?”
宙士又咆吼着。
柏洛米修士银铃似的语声在开始作响;那声响,忠恳而清朗,镇压得全厅都静肃无哗。
“你,宙士,要我说什么呢?你责备我取了火给人类。不错,这火是我给了他们的,我不否认。至于我为什么要帮助人类而和他们为友呢?这,你也许比别人更明白:我从前为什么帮助了你和诸神们,我现在也便要以同样的理由去帮助人类。”
这又刺伤了宙士,他皱着眉不声不响。
“我当初覚得你和你兄弟们受你们父亲的压迫太甚,所以,为了正义与自由,我帮助了你们兄弟,推翻了旧王朝。但自从你们兄弟们创建了新朝以后,你们的凶暴却更甚于前。你父亲克罗士是专制的,但他是个人的独裁。你们这群乳虎,所做却是什么事!去了一个吃人的,却换了无数的吃人的;去了一位专制者,却换来了无数更凶暴的专制者。你,宙士,尤为暴中之暴,专制者中的专制者!你制服了帮助你的大地母亲,你残害了与你无仇的巨人种族,你喜怒无常的肆虐于神们,你无辜的残跛了天眞的童子海泛斯托士;你蹂躏了多少的女神们,仙女们!你以你的力量自恣!倚傍着权威与势力以残横加人而自喜!以他人的痛苦来满足你的心上的残忍的欲望!你这残民以逞的暴主!你这无恶不作的神阀!你说我离开了你,不和你为友,是的,你已不配成为我的友;是的,我是离开了你!我为了正义和自由而号呼,不得不离开你,正和我当初为了正义和自由帮助了你一样!”
他愈说愈激昂。斑白的须边,有几粒汗珠沁出,苍老的双颊,上了红潮,唇边有了白沫,面貌是那么凛然不可侵犯,仿佛他也便是正义和自由的自身。
宙士默默的在听着责骂,未之前闻的慷慨的责骂。在他硬化的良心上,这场当众的责骂,引不起任何同感,却反以这场当众的责骂为深耻。他的双颊也涨红了,双眼圆睁着,手把雷矢握得更紧,——雷声不断的在响,仿佛代他回答,以权威回答正义的责骂——血嘴张得大大的,直似一只要扑向前去捕捉狐兔的勐兽。
海泛斯托士惊得脸色发白,他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厅上的诸神们半声儿也不敢响。
这严重的空气从不曾在神厅上发生过。
五
柏洛米修士山岳似的站立在那里,安详而镇定;他等候最坏的结果,并不躲避。
宙士并没有立时发作。
柏洛米修士又继续的陈说:
“至于我为什么选择了人类为友呢?”
他望了望厅上的诸神,悲戚的说道:
“我要不客气的说了:完全为的是救可怜的人类出于你们的鉄腕之外。人类呻吟在你们这班专制魔王的暴虐之下,已经够久了;你们布置了寒暑的侵凌,秋冬的枯藁;水旱随你们的喜怒而来临,冷暖凭你们的支配而降生;乃至风霜雨露,草木禽兽,无不供你们的驱使,作为你们游戏生杀予夺的大权的表现。为了你们的一怒,不曾使千里的沃土成为赤地么?为了你们的厌恶,不曾在一夜之间,使大水飘没了万家么?雅西娜不曾杀害无辜的女郎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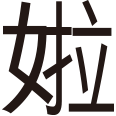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庆么?她死后,不还把她变成蜘蛛,苦扰到今么?日月二神不曾为了他们母亲的眦睚之怨而惨屠妮奥卜所生的十四个少男、少女么?……你们这些专制的魔王们恣用着权威,蹂躏人类,剥夺了一切的幸福与生趣,全无理由,只为了游戏与自己的喜怒。这是应该的么?啊,啊,你们的一部《神谱》,还不是一部蹂躏人权的血书么?无能力的人类,除了对你们祈祷与乞怜,许愿与求赦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趋避之途呢?而你们却以滥用这生杀予夺的大权自喜。以人们可怜的惨酷的牺牲,作为你们嬉笑欢乐之源!假如世界上有正义和公理这东西存在,还能容你们横行到底么!”
庆么?她死后,不还把她变成蜘蛛,苦扰到今么?日月二神不曾为了他们母亲的眦睚之怨而惨屠妮奥卜所生的十四个少男、少女么?……你们这些专制的魔王们恣用着权威,蹂躏人类,剥夺了一切的幸福与生趣,全无理由,只为了游戏与自己的喜怒。这是应该的么?啊,啊,你们的一部《神谱》,还不是一部蹂躏人权的血书么?无能力的人类,除了对你们祈祷与乞怜,许愿与求赦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趋避之途呢?而你们却以滥用这生杀予夺的大权自喜。以人们可怜的惨酷的牺牲,作为你们嬉笑欢乐之源!假如世界上有正义和公理这东西存在,还能容你们横行到底么!”他停顿了一卞,以手拭去额际的汗点。
“你们以为人类便可以永久供你们奴使,永久供你们作为寻求快乐的牺牲品么?这形相不殊于你们,且有更光明的灵魂的人类,难道竟永久压伏在你们专制之下么?不,不,宙士,当你们神之宫里举杯欢宴,细乐铿锵的时候,你们知否人类是如何的在呼吁与愤怒!当你们称心称意在以可怜的被选择的人们作为欢乐的资料的时候,你们知否人类是如何的在诅咒与号泣!”
柏洛米修士睁大了双眼,仿佛他自己也在诅咒,在愤怒。额的中央暴露一条条的靑筋,眼边有些潮湿,语声有些发哑,几要为着人类放声哭一个痛快。
勉强镇定了他自己,又陈说下去:
“这诅咒,这哭声,达到了辽远的我的住所;这哭声,这诅咒,刻刻在刺伤我的良心。我为了正义,为了救人类,老实说,也为自己良心的慰安,我不能不出来做点事。这便是我取了火,一切智慧、工艺的源泉,给了人类的原因。”
恢复了安详而镇定的常态,仿佛大雷雨之后的晴朗的靑天似的,柏洛米修士山岳似的屹立在神厅中,等候着什么事的来监。
石象似的诸神,呆立或呆坐在那厅上;海泛斯托士感动得要哭出来。爱神的嫩脸,羞得通红,她也许正忆起了生平千件的不端的恋爱。雅西娜和月神亚特美丝恨得拖长了她们的靑脸,咬着牙想报复。
宙士频频冷笑着,望望左右立着的权威和势力;他们俩象两支鉄棒似的笔立着,磨拳擦掌的待要发作。
“你说完了话么?我的好心肠的柏洛米修士!现在轮到我的班次了。我不说什么。我要使你明白‘力量’胜过‘巧辩’。来,我的忠仆们!”
权威和势力机械似的应声而立在宙士的面前。
“把他钉在高加索山的史克萨尖峰上,永远的不能解放,为了他好心肠的偷盗。”
鉄匠海泛斯托士低了头,两条泪水象珠串脱了线似的落在地上。他为仁爱喜助的柏洛米修士伤心。
宙士瞥见了这,又生一个恶念。
“而你,我的鉄匠,你去铸打永远不断裂的鉄链,亲自把柏洛米修士钉在那岩上。”
海泛斯托士不敢说什么,低了头走出厅去,诅咒他自己那可诅咒的工作。
六
权威和势力各执着柏洛米修士的一臂向厅外拖。
“停着!”宙士又一转念,叫道。
柏洛米修士的臂被放松了。他安详而镇定的象山岳般的屹立着。
“为了顾念到你从前对于我的有力的帮助,我给你以一个最后的补过的机会:把火从人类那里夺回来,当人类被夺去火的时候,你的罪过也可被赦免。”
柏洛来修士不动情的屹立着,默默不言。
“怎么?不言语?为了猥琐平凡的奴隶,人类,你竟甘心受罪么?”
“不,夺回‘火’的事是不可能的了!我怎么能够‘出尔反尔’的卖友求免呢?这是一。再则,老实说,‘火’是永久要为人类所保有的了。我去,你去,你们都去,都将夺不回来的了。这‘火’在每一个屋隅,在每一个工场,在每一个厨间;在每一个灰堆中,都坚顽的保有着。你们固能毁坏,夺回其一,其二;但你们能把每一个灰堆中的火种都夺去了么?把每一屋里的油灯都毁弃了么?把每一件敲火器都抛到远远的所在去么?不,这是不可能的了!火成为深藏在每一个人心里的知识的源泉。你能把每个人的心都夺去么?火也便是知识的本身,其光明使人类照耀着正义与自由的自覚;你能把人类对于正义与自由的自覚都夺去么?不,这是不可能的事了;——除非毁灭了整个的人类。”
“啊,啊,我便毁灭了整个的人类!”
宙士自负的冷笑道。
“这也是不可能的了。”
“为什么?我也不是曾经毁灭一次人类么?”
“不,这次你是不可能毁灭他们的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火,成为不可克服的了!火使他们知道怎样保护他们自己;怎样为了他们的自由与平等而争斗;火给他们以无量数的智慧,以无穷大的力量。他们将不再向你们这些神阀乞怜,祈祷的了!他们将不再在你们之前逃避,躲藏,求赦的了!他们也不再诅咒,不再哭泣的了!不,他们将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反抗。只要你们敢去和他们争斗,你们将见到他们新的力量的伟大与不可克服。他们将永不再受着你们的奴使与支配;他们要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支配自己,为自己同类而服役,一人为全体而工作,而全体为一人而存在!他们将永不再成为你们娱乐的牺牲,喜怒不常的泄愤的对象;他们要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反抗外来的一切压迫,不,他们的新的力量,还足够撼动神之国的基础的。”
“什么!我将使你知道我的力量。巨人的一族都为我所灭绝,何况猥琐无力的人类。”
宙士气冲冲的说道,但他开始有些气馁,他知道预言者的柏洛米修士的允许是不会落空的。
“不,他们将不再感覚到你的力量的了;巨人族因愚蠢为你们所灭。但人类却将有一个远比你们更伟大,更光明,更快乐的前途;他们对于‘火’的利用,将不是你们这班横暴无智的神阀们所了解的。啊,你们只会把‘火’来照亮夜宴,来幽会,来装饰神的厅与室,来铸打兵器与鉄锁,来作为毁灭敌人的工具。但人类却将‘火’的功用改变了;‘火’将不再是个人的装饰品,将不再是神阀的工具,将不再是阴谋与个人主义的奴役。它幻变了千万个式样,为全人类而服务,为向全人类的光明、幸福的生活的创建之目的而服务。啊,‘火’,我终于见到你是向着最光荣,最正当的使命而服役的了!”
柏洛米修士微仰着头,说教者似的,滔滔的陈说着,为他自己的幻想所沉醉。
“什么!你敢在我面前为人类夸口!”宙士咆哮道。
“这是事实,宙士,你将会知道。”
“好,你等着,你看我将再在一夜之间把整个人类都扫荡到地球以外。”
“不,宙士,不要逞强,这不是你力之所能及。”
“啊,啊,恰是我力之所能及的!”
“不,宙士,不要太自负了;人类已不复是猥琐无力的人类了,从得了火之后,在极短的时间里,他们已使他们自己具有了神以上的新的能力。”
“什么,神以上的能力,你们听听,这不是疯话!”
宙士向左右的诸神望望,诸神机械似的点点头。
“我几曾有过‘超事实’的允许!”预言者的柏洛米修士悬切的说道。
“随你的意思去允许什么吧,我是决意将要扫荡那批猥琐的人类的了。”
“你不能,宙士。”
“我能,柏洛米修士。”
“绝对的不能,我说。”
“绝对的能!我说。”
他们之间,几乎是斗嘴的姿态。
“当你们敢去和人类发生新的斗争的时候,宙士,被扫荡出大地以外的将是你们而不是人类。”
柏洛米修士安详而镇定的预言道。
“什么!你这暴徒!敢!”
宙士再也忍不住,大声咆吼道,整个神之厅都为之一震。
“来,把这叛逆带到高加索山去!”
权威和势力各执着柏洛米修士的一臂,向外推,形相狰狞得怕人。
“我因了帮助有伟大的前途的人类而受到苦难,我不以为憾。柏洛米修士安详而镇定的回过头对宙士说道。“但,宙士,你的权威的发挥,将以我的牺牲为最后的了!”
“什么!”
宙士的愤怒的水闸整个的拉开了;他忘其所以的,双足重重的顿着,紧紧的把握着雷矢的那只手,在桌上重重的击了一下。一声震天动地的霹雳,烟火和硫磺气弥漫了整个神之厅。爱神爱孚洛特蒂惊得晕倒了;丘比特大叫的藏在椅下。宙士他自己也被震得耳聋。神之后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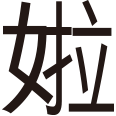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幽幽的哭了。雅西娜还是石象似的站立着。但她靑色的脸部却笼罩上一层未之前有的殷忧之色。
幽幽的哭了。雅西娜还是石象似的站立着。但她靑色的脸部却笼罩上一层未之前有的殷忧之色。雷声不断的大作,电光在闪,每一电鞭,都长长的经过半个天空。铅灰色的天空,重重的为破碎的绵絮似的雨云所笼罩。大雨倾盆的倒下去。
大雷雨象永不停止似的在倾泄,仿佛在尽量的表演神阀的最后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