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埃那克河緩緩的流過平原,流過山谷。水聲潺潺的悠揚的歌唱着。河邊的靑草,絨氈似的平鋪着。未知名的黃花、白花、紅花、藍花,無秩序的挺生於細草之間,仰面向着太陽和天空,驕傲而快樂,彷彿這大地,這世界便是屬於它們似的。古老的橡樹經歷了不知年代的歲月,和這河水同樣的顯得蒼老,張開杈椏的老幹,萬事無所用心的在太陽底下曝曬取暖。藤蘿爬滿了它的身上,居高臨下,悠然自得的欣賞這大自然的美景。一株新生的常春藤懸掛着婀嫋多姿的柔條,恰好拖在水面之上,臨波自照它的綠顏,嬌媚若嫁前一夕的少女,春風吹之,柔條亂動的乘機賣弄風姿,水中的長影,也拂移不已。游魚三五,正集其下,受了這不意的驚擾,紛紛的四竄而去,平靜的河面上便連連起了數陣漣漪。
河神埃那克士的獨生女兒埃娥常在這河邊草地遊戲着。她是一位初成熟的女郞,雙頰紅得象蓓蕾剛放的玫瑰花,臉上永遠的掛着微笑。編貝似的一排白齒,那麼可愛的時時的微露着,一雙積伶積俐的眼珠兒,那麼樣天眞爛漫,足以移動了最兇暴的神與人的胸中所蘊的毒念。一對白嫩而微現紅色的裸足,常在這草地上飛跑,細草低了頭承受着她的踐踏,彷彿也感得酣適的蜜意。
她是她父親埃那克士的安慰,他的驕傲。他也常坐在河邊的石塊上望着她在天眞的奔跑着;凝注着她的漂亮的背影,他自己也爲之神移心醉。
“誰是她有福的郞君呢?該好好的替她揀選一個纔好。”老埃那克士微笑的滿足的自語着。
埃娥常常找了許許多多的小花朵兒,滿手把握不了,強迫的戴些在她爸爸的白髮上,老埃那克士象小孩兒似的婉婉的隨她插弄。
這一片快樂的天地是他們的,純然的屬於他們。
二
但有一天,一個闖入者突來打斷了他們這快樂的好夢。
埃娥在草地上飛跑着,嬉笑的彎身在採擷小花朵兒。她爸爸恰好有事,不曾和她同來。
她跑得更遠更遠的離開了河邊。
暮靄絢麗的現在天空,黑夜的陰影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偸偸的跑到大地上來。晚風吹得埃娥身上有些發涼。
她想,這該是歸去的時候了。
剛回過身去,她發現了一個身軀高大的神,如大樹幹似的,矗立在蒼茫的暮色之中,正擋着她的歸途。
兩隻熱情的眼,灼灼的凝注在她的身上。
她的雙頰立刻集中了紅血,覚得有些發熱。
她想越過這位不意的來客。假裝着從容不迫的向他走了去。心頭是打鼓似的在跳着。
轉了過去,她發現那兩隻灼灼的熱情的眼,也隨了她而轉。她有些發慌,心跳得更厲害,彷彿要衝到口腔中來。
離了那個高大的身軀彷彿很遠了,她放慢了足步,偵探似的偸偸側轉頭去。
啊,這高大的身軀是緊跟在她後邊!
她望見那兩隻灼灼的熱情的眼,象天上的“黃昏曉”似的老凝注在她身上。
“完了。”她自己警覚的暗叫道。立刻飛步的向家而逃。然而全身在發抖,雙腿軟軟的,有點不得勁兒。愈奔愈快,呼吸急迫得接不上氣來。臉是緋紅的。身後也有飛跑着的沉重的足音。她什麼都不想,只是沒命的奔逃。頭有些發脹,要暈倒。
後邊是緊跟着的足步聲。
實在是透不過氣來,膝蓋頭酸疲得要融化了。被一個小石子絆了一交。她全身的倒在地上。臉色由紅而變白。
黑夜遮蓋了一切。
三
那兩隻灼灼的熱情眼,如今是更貪婪的注射在她的眼。她閉上了眼皮。淚不自禁的撲撲的落下,如連綿的秋雨。
“噯,不要傷心了;隨了我,什麼都如願。”那高大的身軀擁抱着她,他身上是那麼熱而有力,彷彿被圍困在熱度過高的溫室裏,彷彿被壓榨在千鈞的岩石之下。
她的紅血復潮上了雙頰。
女性的同感的溫柔漸漸的伸出頭來。
她掛着殘淚的臉漸漸的消失了恐怖。她不再掙扎,不再戰慄,不再想躲避。她被男性的熱力所克服。
她如做了一場惡夢;嘆了一口氣,從夢中醒來似的張開了眼,同時支持自己的要脫出他的懷抱。
在掙脫着,柔嫩的手背,不意的觸到了他的頷下,有些麻叮似的刺痛。
她吃了一驚。那頷下是一部鬑鬑的短髭。
她和他面對着面的望着。
好可怕的一張峻澀而蒼老的臉,只有那雙眼光是灼灼的熱情的。
她若遇蛇蠍似的竭力掙出他的擁抱。她的心頭既熱而又冷下去。想要作嘔。頭目涔涔然的。
她背轉了身,渾身若發瘧疾似的在亂抖。那高大的身軀作勢的還想擁抱她。
但她聚集了全身的勇氣,轉過身去,和他面對面的,嚴峻而帶哭聲的問道:
“你是誰?”
那高大的身軀若夜棲於秋塘間的鷺鷥似的格格的笑着;這奸笑,使埃娥的血都冰結了似的凝住了;渾身的毛孔彷彿都張大了,吐出冷氣來。
“孩子,啊,啊,你不知道我麼?”充滿着自負的威權的口吻。他的手撫拍着她的右肩。
她蛇似的滑開了他的接觸。
“孩子,啊,啊,你要知道,你該怎樣的喜歡呢?”他的手又開始去撫摸她的裸出的背的上部。
“不,不,”她聳肩的拒絕了他,含煳的答道,自己也不知道說出的是什麼聲音,本意是要冷峻的直捷痛快的說道,“不喜歡,不喜歡,一百個不喜歡!”
還是溫和的追求着,“啊,啊,孩子,你有了一個人與神之間最有權威的情人了,”那充分的自負的聲音。
“宙士!”埃娥驚喊了起來,幾乎忘形的。她又要掙扎的轉過身去,飛步逃走。
然而她渾身是沒有一點兒的氣力。
“是宙士,我便是他!”那高大的身軀的神,傲然的答道,“你該以此自傲。”
“不,不,”埃娥欲泣的在推卻,彷彿對於一切都顯出峻拒的方式,神智有點昏亂。
宙士作勢又要把她攬到懷中來。她蛇似的亂鑽,亂推,亂躲。
“怎麼?難道你竟不願意有這樣一個情人麼?”
他覚得有些受傷。
埃娥一腔的怒氣,臉色變得鉄靑的,顫巍巍戰抖抖的斷續的努力的說道——幾乎是聲嘶力竭的在喊叫。
“是,不願意……就爲了你是宙士……你這惡魔……你又來蹂躪……人間的多少好女子……嗚嗚!都供了你的淫慾的……犧牲!”她變成了哭泣,“嗚,嗚,那可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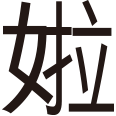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託娜(Latona),她被你所誘,爲你生了那一對雙生子女,你的妻竟拒絕了她在大地上生產……嗚!你這淫賊……你竟不一加援手!……讓她在浮島的狄洛斯(Delos)上住着……而賽美爾(Scmele)……那女郞犧牲得更酷毒……更悲慘……嗚,我不知你是否有一點兒感情……有一些兒心肝在腹腔中!……你完全爲了你的淫慾……她懷了狄奧尼修士在身,受了你的妻的欺騙……被你自己的雷火所燒灼……你在火中只搶救了孩子出來……那母親……可憐的竟被燒死……”她動了同感,竟哀哀的大哭起來,停了一會,勉強的止住了嗚咽,眼射出正義之光,繼續的說着,反而鎮定了些,不再那末戰抖得厲害。“那位絕代美女的狄娜(Danaë),她被囚在鉄塔之中……而你……爲了自私……化了一道金光,入塔與她同居。……她生了一個孩子……你完全棄之不顧……她被她父親所棄,……連孩子被裝在筒中,拋入大海……她怎樣的向你求救……她怎樣的禱求着你……她向天伸出雙手……她說了怎樣無數的懇求的話,……你幾曾答理她……你這自私的無恥的……”
託娜(Latona),她被你所誘,爲你生了那一對雙生子女,你的妻竟拒絕了她在大地上生產……嗚!你這淫賊……你竟不一加援手!……讓她在浮島的狄洛斯(Delos)上住着……而賽美爾(Scmele)……那女郞犧牲得更酷毒……更悲慘……嗚,我不知你是否有一點兒感情……有一些兒心肝在腹腔中!……你完全爲了你的淫慾……她懷了狄奧尼修士在身,受了你的妻的欺騙……被你自己的雷火所燒灼……你在火中只搶救了孩子出來……那母親……可憐的竟被燒死……”她動了同感,竟哀哀的大哭起來,停了一會,勉強的止住了嗚咽,眼射出正義之光,繼續的說着,反而鎮定了些,不再那末戰抖得厲害。“那位絕代美女的狄娜(Danaë),她被囚在鉄塔之中……而你……爲了自私……化了一道金光,入塔與她同居。……她生了一個孩子……你完全棄之不顧……她被她父親所棄,……連孩子被裝在筒中,拋入大海……她怎樣的向你求救……她怎樣的禱求着你……她向天伸出雙手……她說了怎樣無數的懇求的話,……你幾曾答理她……你這自私的無恥的……”她以一手戟指着他,幾乎是在謾罵。
宙士並不曾發怒——並不曾如他平日似的那末容易發怒——但他也不曾爲這一席話所感動,那眞性情已經涸乾到半滴不存的心腔,是決不會知道自愧,自省的,反而見了這美麗的少女,埃娥,時而戰慄,時而哭,時而罵,時而憤怒的種種姿態,而感到醉心;就是在悲恐裏,憤怒裏,她的丰姿也不曾減少半分。那少女的憤激的美,宙士是從未見到過的,幾乎若欣賞什麼似的,他是在嬉嬉的靜覌默察着,沉醉到忘記了一切,連她罵的什麼,也都模模煳煳的。
“說完了嗎,孩子?”宙士嬉嬉的接說道。
埃娥覚得心頭舒暢了些,默默的不理他。
“怎樣?現在跟我走嗎?”他如對付小孩子似的哄逗着她。
她突然的又一驚,“不,不!”她說道,想逃避。
但她怎樣逃得出宙士的掌握呢?
新月掛在藍色的天邊,爲這場劫掠婚作證人。
四
老埃那克士那天很晚的方回家來。他想,他的孩子埃娥該早也在家裏等候着他了,她該如往常的跳躍着出來歡迎他,抱住他的頭頸,吻他的冰冷的面頰。想到這,他不自制的微笑着。她還該象往常的故意放刁,故意撒嬌,絮絮切切的責備他爲什麼那麼晚纔回家,張大了她的嬌媚的小口……害她老等着,她餓得慌了……她餓得幾乎要想吃人……她還要編造出一大篇故事來告訴他……她怎樣的在草地上遇到了一條毒蛇,她奔逃跌了一交,“你,看,這裏是血!”或者她便訴說,怎樣的在採擷草花的時候,有一個怪模怪樣的羊足的薩蒂兒在追求着她,怎樣緊跟在她後邊說些什麼混賬的話,害得她不得不掩了雙耳逃歸……一切都只爲了他不和她在一處。而他便緊緊的摟抱她在胸前,如她孩子時代似的,拍拍她,哄哄她,說爸爸不再離開她了,都是爸的不好。乖乖的,明兒找個好的漂亮的女婿兒給她,而她急速的掙出了他的懷抱,嬌嗔的奔進屋去,故意兒嘭的一聲,重重的關上了房門。
一縷甜蜜的家庭的樂感,在他心腔裏飄蕩着。
老埃那克士故意放輕了足步,當他走近了家的時候,要出其不意的嚇那頑皮的埃娥一跳。他一步步走近了,走到門邊。埃娥不在那裏!
“這孩子,今天怎麼不在門邊等爸?”預籌的打鬧的計劃爲之粉碎。他有些慍惱,重重的踏着步走進。
埃娥也不在廳堂裏。
“埃娥!”老頭兒粗聲的叫道。沒有迴應。
急速的走到她的房門口,以爲她偶然疲倦了在睡。
從門縫裏伸進了白髮的頭顱,柔聲的說道:
“埃娥,起來,爸回來了。還在睡!你這懶孩子!你看,爸爲你帶了什麼好東西來了?……”
他在星空和新月的朦朧的微光之下,看得淸楚,牀上並沒有埃娥。被褥是齊整的堆疊在那裏。
“埃娥到哪裏去了呢?”
他怔住了。心裏開始有些惶惶。
“不要躲起來嚇我,天黑了!我的埃娥,好埃娥!”他悽然的叫道,還疑心她故意躲藏了起來。
“埃娥,埃娥,”他大聲的叫道。還是沒有迴應。
“你到哪裏去了,埃娥?”什麼屋角門邊都找到了,沒有一個人影兒!
“埃娥,埃娥,埃娥!”他找到門口,“埃娥,埃娥!”他往屋後找。都沒有迴應。
他心頭涌起了亡失的預警。他知道埃娥從不會那麼晚回家的。
“埃娥,埃娥,埃娥!”他的叫聲淒厲的自己消滅於黑暗中。
他提了一盞手提燈,龍鍾的走到河岸的草原上。老橡樹象鬼怪似的矗立於大地之上。天空晶藍得象千迭琉璃的凝合;星光疏朗朗的散綴於上。鐮刀似的新月,已走在西方的天空上,很快的便要沉沒下去。
老埃那克士無心領略這可愛的夜景。他走一步叫一聲。“埃娥,埃娥,埃娥!”大地和夜天把這可憐的呼喚呑沒進去,一點回聲都沒有。
“埃娥,埃娥,埃娥,你在哪裏?”老頭兒悽惶的叫道。
他叫着,他叫着,連棲在老樹上的夜鴉都爲之驚醒,拍着雙翼,很不高興似的哌哌的叫着,遠遠的飛向別的地方去繼續它們的好夢。
“埃娥,埃娥,埃娥!”這呼喚空曠而無補的自己消沉下去,象海水之齧咬巖根,嗡嗡作響似的無聊賴。
他叫得喉幹,他叫得脣顫,最後,幾乎成了乾號,有聲無力的喘息着,癱坐在草地上。
“她是亡失了!她是亡失了!”老埃那克士想道;嘆息着,有一個最壞的結果的預測。
“爲毒蛇所咬傷?……然而沒有她的呻吟,她的蹤影。落到什麼懸巖之下,跌死了……也許可能……”
但他不敢想到……被什麼淫惡的神或人劫掠而去……美麗便是禍端……天涯水角,他到什麼地方去尋找呢?父女還有相見的時候麼?
他絕望,他的心有什麼在刺痛;他哀哀的哭了。他的滔滔的淚水,混在埃那克河水裏,流去,流去,流到不知所在的地域。
他躲在深屋之中,沉默的在愁思;他瘋狂似的在草地上漫走着;他若有所失的懶散的坐在河岸的石上,雙眼茫然的望着遠處,望着那夕陽西沉的無垠的天涯。
五
就在那夕陽西沉的天涯的一角,宙士安放了美麗的埃娥,以備他政躬閒暇的時候的享用;活象一個孔雀,一隻梅花鹿,只是被囚著作爲覌賞之資。
雖然是衣食不缺;住的是高房大廈,使喚的是豪奴俊婢,但埃娥是終日的悲哀着。
那討厭的宙士,她一見了便要嘔心,便要憤怒,便要躲藏。他卻偏要不時的來糾纏着她。被玩弄着的美人兒的她,如今是那麼容易激怒,雖然她往日是那麼溫柔可喜。宙士,殘忍的宙士,卻反以她的淚水,滿臉橫流直淌的淚水,作爲覌賞的對象,竟說,他最愛看她的發怒作態時候的嬌憨模樣兒。調獸者還不是偏要挑逗着被囚的獸類的使性以爲快樂麼?
她想哭個痛快,但眼淚是常被憤怒之火燒灼得幹了;她想投身於什麼高崖絕壁之下自殺,然而宙士的奴隸防衛得那麼嚴密……而且她父親還不知道她的生死……
一想到她父親,她的心又軟了下來。年老的爸,發見了她亡失了時,還不知要怎樣的悲哀呢!他該天天在念着她,在默默的愁苦着吧。有什麼方法向他通一個信呢?有什麼法子告訴他一聲:“你愛的女兒並不曾死,她不過被暴主所囚禁着,你設法救出她吧;至少,你該設法來見她。”
他知道了她的確消息的時候,該是怎樣的高興呀!緊蹙不開的雙眉也將暫時爲之一放吧。她總須設法和他通一個音訊的。
然而有什麼方法可通音訊呢?宙士的奴隸們監視得那麼嚴密,連房門,她也難得走出一步。
在想到她要是有機會能夠見到她爸爸呀,他們將緊緊的摟抱着,互以樂極而涕的淚臉互相倚偎着;她將對他痛快的傾吐出所受的那一切的冤抑,她在世界上至少是有一個安慰她眞心的疼愛她的人,然而這唯一的慰藉,卻也是空想!
她幽幽的哭了。
宙士又偸偸的由什麼地方滑到她的身邊來。
“你又在哭!”
她別轉頭不理他。但宙士勉強的擁着她,玩物似的慰勸她,逗弄她。這逗弄增益了她的愁恨。
她愈躲,宙士迫得愈緊,逗得愈高興。
“那麼美的天氣,我們倆到園囿裏去走走嗎?老悶在屋裏要悶出病來的。”宙士勸誘着她。
實在,她也好久不曾見到天日了,聽了這話,只默默的不響;宙士覚察出她的默允,便以一臂夾了她的臂,半扶掖的把她帶到了園囿中。
花朵爭妍鬥豔的向春光獻媚;老大的綠樹是那麼有精神的矗立着,象整排的兵在等候命令。地下是那麼柔軟的草氈,足履悄然無聲。
和大自然雖只隔絕了幾天,在埃娥看來,好象是十月數年不曾相見似的。一切都顯得親切而可愛。如久別重逢的親友。那黃澄澄的太陽光,竟如此的輝麗,在臉上手背上撫摩着,是如此的溫柔,彷彿她從不曾有過那麼可愛的白晝。
數級的雲石的踏步引他們到一泓池水的邊涯。這池水是如此的淸瑩,如此的澄綠,如此的靜靜的躺着,竟使人不忍用手去觸動它,連把身體映照在水面也似是有礙這靜默的繼續。水底有幾株鮮翠欲滴的水草,秀挺而又溫柔的各自孤立着。一樹紫藤的珠串似的花叢,正倒影在池中。
埃娥默默的坐在這池邊,不言不動,她爲這靜默的幽寂所吸引,暫時忘記了她的煩惱,忘記了她的存在,乃至也忘記了攬抱着她的宙士。
宙士彷彿也爲這沉默所感動,雙眼凝注在天空,好久不曾說什麼,天上是纖雲俱空,似是一塵不染的水晶板。
“嘎,”宙士突然的大叫了起來;他連忙推開了埃娥,立起身來,急速的召集一大片的厚而重的烏雲,遮蔽了那淸天。他看見遠遠的東天,有孔雀的斑斕的羽光在一閃一閃的動着。
埃娥的幻默被打斷,驚愕的也立了起來。她呆了似的,不知有什麼變故要發生。
宙士口中念念有辭,把池水潑了一握在她身上,叫道:
“變,變!”
等不及埃娥的覚省,她已經變成了一隻潔白無垢的牝牛站在那草地上,黑漆似的雙睛,黑漆似的有亮光的雙角,黑漆似的堅硬的四蹄,襯托着一身細膩的白毛,這是神與人所最喜愛的牲畜。
天上的黑雲已經披離的四散了;孔雀的尾翎,儀態萬方的在空中放射着光彩。池水被映照得有些眩目憷心;和這幽悄的環境,絕不相稱。
孔雀的主,神之後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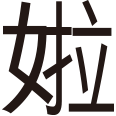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臉若冰霜的和她的不忠實的丈夫,宙士,面對面的站着。她明白她丈夫耍了什麼一個把戲。好幾天以來,她已覚察到他的神情不屬的可疑的樣子。一忽兒的工夫,他又不見了,宮中,廳上,都找不到,行蹤飄忽得象六月的颶風。說話老是唯唯諾諾的。該辦的正事全都放下了。
,臉若冰霜的和她的不忠實的丈夫,宙士,面對面的站着。她明白她丈夫耍了什麼一個把戲。好幾天以來,她已覚察到他的神情不屬的可疑的樣子。一忽兒的工夫,他又不見了,宮中,廳上,都找不到,行蹤飄忽得象六月的颶風。說話老是唯唯諾諾的。該辦的正事全都放下了。有什麼羈絆着他呢?
愛孚洛特蒂和她的頑皮的孩子丘比得常常竊竊的私語着;丘比得對着宙士作鬼臉。他怒之以目,微微的對他搖頭。雅西娜石象似的站在那裏,以冷眼作旁覌。
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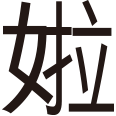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坐在那裏,什麼事都看在眼裏,明白在心裏,表面上只裝作不知。但她已遣了無數的偵探,在跟隨着宙士。早已把宙士這場喜事打探得明明白白。
坐在那裏,什麼事都看在眼裏,明白在心裏,表面上只裝作不知。但她已遣了無數的偵探,在跟隨着宙士。早已把宙士這場喜事打探得明明白白。如今是捉個空兒來點破他。
宙士奸滑的微笑着,並不說什麼。老練於作奸犯科的心靈,已不知什麼叫羞愧。他在等候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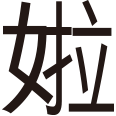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的發作。
的發作。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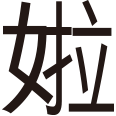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洞若覌火的,立刻奔到白牛的旁邊,裝作愛悅的撫拍着她,說道:
洞若覌火的,立刻奔到白牛的旁邊,裝作愛悅的撫拍着她,說道:“好不可愛的白牛!是你所畜的麼?”
宙士點點頭。
“我要向你要個小惠,把這匹白牛送給了我罷?”
這使宙士很爲難的躊躇着;給了她罷,埃娥是從此失去;不給了她,將再有可怕的事在後面。
但巧於自謀的宙士,只一轉念,便決定了主意,裝作淡然的,微笑說道:
“你既然愛她,便屬於你罷。”
那付得失無所容心的瀟灑的態度,活畫出一位老奸巨滑的久享榮華的“主兒”的神情。
好象博弈負了一場似的,他聳聳肩走了;也許已另在打別一位可憐的女郞的主意。留下埃娥聽任他的妻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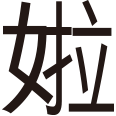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的處置,播弄,與虐待。
的處置,播弄,與虐待。豪富的玩獸者,誰還顧惜到被玩弄的獸類的生與死,苦與樂呢?世間有的是獸類!
六
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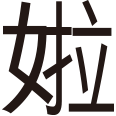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冷笑的目送宙士走去。她不敢惹宙士的生氣,卻把久鬱的妒忌與憤怒全盤傾倒在可憐的埃娥的身上。
冷笑的目送宙士走去。她不敢惹宙士的生氣,卻把久鬱的妒忌與憤怒全盤傾倒在可憐的埃娥的身上。埃娥的身體雖變了牛,但她的心還是人心,她的耳也還是人耳。她呆立着視察這一幕滑稽劇的表演,無限的傷心,不禁的淌下淚來。
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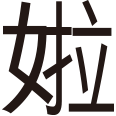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見白牛落淚,還以爲是惜別,這更熾了她的無明的妒火。
見白牛落淚,還以爲是惜別,這更熾了她的無明的妒火。“你這無恥的賤奴,慣勾引人家丈夫的,還哭麼?”她用力拳擊埃娥一下;打得那麼沉重,牛身竟爲之倒退幾步。
埃娥想告訴她,這完全是她丈夫的過失,她自己並不甘心服從他,她並不愛他,這些事全然與她無干。她是一位可憐的少女,被屈服於他的暴力之下而無可如何的。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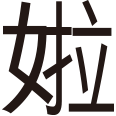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應該憐恤她,同情她,釋放她回去看望她的父親。她父親自她亡失後,必定天天在愁苦,白髮不知添了多少,淚水不知淌了多少。該看在同是被壓迫的女性的分上,從輕的發落她!……
應該憐恤她,同情她,釋放她回去看望她的父親。她父親自她亡失後,必定天天在愁苦,白髮不知添了多少,淚水不知淌了多少。該看在同是被壓迫的女性的分上,從輕的發落她!……她想說千萬句的話,她想傾吐出最沉痛的心腑之所蓄,但是她只是吽吽的鳴叫着,說不出一句話來!
她於着急的後足亂蹦亂跳;她要伸出雙手來呼籲,乞求,懇禱,但是她的手已變了前蹄!她想跪下去,抱了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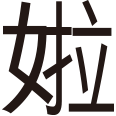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的腿,吻着她,要以女性的痛苦,贏得女性的憐恤與同情,但是她如今是變成了牛,什麼都不能如意的行動。
的腿,吻着她,要以女性的痛苦,贏得女性的憐恤與同情,但是她如今是變成了牛,什麼都不能如意的行動。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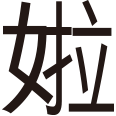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還以爲她是在拗強,在掙扎,在敵對,憤怒更甚,拳擊得更重更快,一直打到白牛跪倒在地上,她自己也手臂痠痛,無力再打,才停止了。
還以爲她是在拗強,在掙扎,在敵對,憤怒更甚,拳擊得更重更快,一直打到白牛跪倒在地上,她自己也手臂痠痛,無力再打,才停止了。“你這賤婢,苦處還在後呢,現在且讓你偸生苟息一下!”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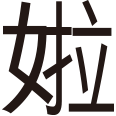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臉色蒼白的,喘息的說道:
臉色蒼白的,喘息的說道:“來!百眼的亞哥斯。”
她的跟從者百眼怪亞哥斯垂手聽她的吩咐。
“把這賤婢好好的看守着,永遠跟在她的後邊,一刻都不許逃出你的視線之外。不許任何人與神接觸着她。你要賄縱,當心我的家法!”
百眼怪諾諾連聲。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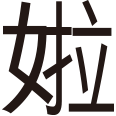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恨恨的走了,還回頭指着白牛罵道:
恨恨的走了,還回頭指着白牛罵道:“你這賤婢,且看我的手段,要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埃娥不能剖白一句,只是將萬斛的悲淚向腹中自呑下去。她不再說什麼,殘酷的宙士竟將她的口永遠封鎖着。她只能沉默的啞子似的忍受一切。
“這惡毒之極的淫棍!”她想切齒的罵道,而發出來的聲音卻變作吽吽的鳴叫。
百眼怪亞哥斯,頭臉上生長着一百隻眼,每兩隻眼輪流着休閉,那九十八隻的灼灼的看守的眼,老是日夜警覚的監視着她。
一步不離的監視,驅趕,這百眼怪的亞哥斯。
埃娥這樣過着牛的生活,而她的心卻是人的心,她的感覚卻是人的感覚。
每逢走到水邊,她便想竄入水底,了此沉痛的生命,而百眼怪卻永遠牽率着她,嚴厲的監視着,呼叱着;使她死也沒有自由。
七
求死不得的埃娥,捱過着畜類的生活,度一日如一年,乃至十年百年。她僅有一條思念,便是她的父親,僅有的一個願望,便是飄泊的走到埃那克河畔,見她父親一面;只要能夠見她親愛的父親一面呀,便萬死,便受比這更楚毒萬倍的楚毒,她也甘心!
她是這樣掙扎的捱過着畜類的生活,一天又一天的,受了多少的鞭撲,呼叱,楚毒,然而阻止不了她步步向埃那克河而去,便一天只走一步,她也高興。
不知有多少時候了,埃娥的願望居然得償。當她遠遠的望見一條白練似的埃那克河蜿曲的在山下流動着時,她便渴想要飛奔而去。她快樂得下淚。然而繩兒是被牽在百眼怪亞哥斯的手上。她愈掙扎的要向河而趨,那忠心的神奴亞哥斯卻偏將她拉回山谷。她向前一步,倒被拉回三步。
親愛的父親,只是可望而不可即;親愛的童年嬉遊之地,孩子時候生長的快樂的家,已可奔就,卻只是可望而不可即。她焦灼得如被架在火堆上燒烤。
愈急愈緩,愈掙扎,愈受阻難。
索性鎮定了下去。強抑住萬斛的悲哀與思慕。
有意無意的向下而趨。亞哥斯永遠跟隨着她。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埃娥是踏在她所愛的草地上了,切切實實的踏到了她的家鄉了。
看啊,河邊的大石上,坐着一位老頭兒,垂着頭,若有深思,一切對於他似都無見。白髮,在風中飄蕩着。
“不是爸爸嗎?”埃娥想大叫起來,然而只是吽吽的幾聲牛鳴。
她想高聲的說道:“爸呀,你的寶貝回來!看呀,她在這邊呢!你爲什麼不擡起頭來?爲什麼不向這邊看?”然而發出的只是幾聲吽吽的牛鳴。
她的心狂跳着,她的淚不自禁的直淌下來,她跳躍,她奔騰,什麼都阻止她不住,她要奔過去緊緊的擁抱了她的父親,痛快的大哭一場,儘量的訴說這別後所受的無涯無限的楚毒與屈辱。
然而繩兒是被牽在亞哥斯的手上!
她實在再忍受不住了;這當前的相逢,這經了長久的思慕的相念,這渴想已久的親戀的撫慰,痛苦的傾吐,豈能再讓它滑了過去!她不顧一切的,在掙扎,在奔騰,在爭持。
繩兒終於被她在百眼怪亞哥斯的手上掙脫。她迅如電似的沒命的向她父親身邊奔去,蹄底踢起了一陣泥霧。亞哥斯追在後面,趕她不上。
她喘息的奔到了埃那克士身邊,溫熱的鼻息直噴衝到他的臉上。老頭兒詫異的站了起來。這可愛的白牛爲什麼奔跑到他的身旁呢:這主什麼徵兆呢?難道是女兒遣送她來的?該有女兒的消息吧?——他一心只牽掛在女兒身上!
埃娥渴想伸出雙手來抱住她爸爸的頭頸;然而可憐她的雙手變成了牛的前蹄,竟不能伸出擁抱他,她高聲的悲痛的叫道:“爸爸,爸爸,”而這叫聲也竟變成了牛鳴。老頭兒木然的站在那裏,不明白這白牛的意思。
埃娥悲楚的叫道:“爸爸,爸爸,你失去的女兒在這裏了;她冒了千辛萬苦而來到你身旁;你爲何不擁抱她呢?”然而只是變成幾聲吽吽的牛鳴!
百眼怪遠遠的在追來了;她又焦急的說道:“爸爸,爸爸,快些,我對你說,那邊有人追來了!我要對你說些要緊的話,爸爸,爸爸!”
然而只是連續的吽吽之聲;老頭兒還是木然的站在那裏,一點表示都沒有——他自從失去了愛女,老是這樣木木訥訥的,對於一切都不發生興趣。
急得埃娥雙淚直流,雙蹄在泥地上踐跳不已。
老埃那克士注意到牛的眼淚,他開始覚得有點怪。
然而埃娥老說不出話來,只是連續的吽吽的叫着。
她詛咒那殘酷已極的宙士!切齒的咒着,恨着。
亞哥斯快到眼前了,他們還不能通達一點的意見。
突然,埃娥想到了一點很好的主意:她用前蹄在泥土上劃出字來。
“我是埃娥,爸爸,我是埃娥!”
老埃那克士見了這牛所劃的字跡,大叫着的把白牛緊緊的抱着,比遭到死喪更沉痛的“兒呀,兒呀”的哭喚着。他的臉和白牛的臉緊緊的貼着;熱淚交雜的流下,辨不清誰的;他的胸膛和白牛的側胸緊緊的依偎着,兩個心臟都在狂跳。他的雙手緊緊的用全力的抱住了埃娥的頭頸。然而埃娥卻沒有法子可以對她爸爸表示什麼;她只是緊緊的用細毛叢叢的身體挨擦着她爸爸的身體。
辨不出是喜,是悲,是苦,是樂!一霎時的熱情的傾吐,千萬種愁緒的奔泄!
而百眼怪亞哥斯來了,他便要把白牛牽走。老埃那克士將身體攔護着她,白牛也輾轉的躲避着,不受他的羈拉。
老埃那克士一邊沒口的向百眼怪亞哥斯懇求着,什麼悲惻的懇求的話,什麼卑躬屈節的祈禱的要求,都不揀不擇的傾泄出來。
“求你,求你……天神……上帝……她是我的女兒……讓我們說幾句話……上帝……我的天……我所崇拜的……我求你……求你……求你……”
他一手攔阻亞哥斯,一手作勢向天禱求,而雙膝是不自禁的跪倒在地上。白牛在閃避,躲藏,卻老依偎在她父親的身旁。
神之奴都是鉄打石刻的心肝。亞哥斯見了這位白髮蕭蕭的老人這樣沉痛的呼籲,他卻是不動心,雖然任誰見了都要爲之感動得哭了。
他手打足踢的要把老頭兒推開,他要乘機的拉起白牛的繩兒來,牽着便走。
然而老頭兒抵死的在阻擋着;白牛是那麼巧滑的在閃避。
引得亞哥斯心頭火起。捉一個空,他把牽牛的繩獲到手裏,便盡力的拖了走。
埃娥忍着萬不能忍受的痛苦,死賴着不肯走,只要多停留一刻,她也心滿意足。挨一刻是一刻!
老埃那克士是死命的抱着牛頸,死也不放,白牛被牽前一步,他也隨走一步。他哭喊不出聲音來;眼淚也被熱情與憤急燒乾得流不出來。那一對可怕的預備拼了命來護救他所最愛的女兒的眼,活象瘋人的似的。不知道哪裏來的力氣,衰老的老頭兒竟成了一位勇勐無比的壯士。
但亞哥斯用打牛的鞭去鞭他,用足去踢他,渾身受了不輕的傷,但他還是跟着,抱了白牛的頭頸不放手。
埃娥是如被白熱以上的地獄的火所燒灼,她憤怒得雙眼全紅了,她的後蹄沒命的向亞哥斯腿上踢。
這最沉痛的活劇不知繼續到多少時候,但老埃那克士終於放了手。他頹然的跌倒在地,不知生與死,白牛是被鞭被牽的遠遠的離去。
八
白牛發了狂。她瘋狂的脫出了百眼怪亞哥斯的羈勒。她是那樣的可怕,實在連兇暴若魔王自己的亞哥斯也不敢走近她身邊。她奔騰,她跳躍,她越山過嶺,她竄林渡河,遠遠的,遠遠的,向着無人跡的荒原奔去。
亞哥斯追不上她。
她不知奔跑了多少里路,不知越過多少的城邑與山林,不知經歷了多少的風霜與雨露,落日與殘星。她一息不停的跑着,如具有萬鈞之力。
不知什麼時候,她停止了;而停止時,她的瘋狂便清醒了些。她開始在靑草地上吃草,在河裏喝水。她模模煳煳的想到她過去的一切。
而回想便是創痛。她的清淚,綿綿不斷的滴在河裏。她沒有什麼前途:她沒有什麼光明的結局的空想,她只有一個願望,她只有一個咒詛,她只有一條心腸:
她要報復!
這使她不願意死:死要死個值得;對敵人報復了才死,就是一個最殘酷的死,她也含笑忍受。
她要報復!爲她自己,也爲了一切受難的女性!
她不知將怎樣的報復,然而她有一個信念:她知道,總會有這麼一天,“天國”是粉碎了,粉碎在她和她的子孫之手。
這信念,堅固了她的意志,維持着她的生命,使她受一切苦而不想以“死”來躲避。
但有一天,新的磨難又來臨。不知怎樣,神後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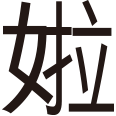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又發見了她在草地上漫遊,而百眼怪亞哥斯已不在她身邊監視着,便大怒,切齒的恨道:
又發見了她在草地上漫遊,而百眼怪亞哥斯已不在她身邊監視着,便大怒,切齒的恨道:“這賤婢,且看她還會逃出我的掌握不?”
她遣送了惡毒的牛蠅到埃娥的身上,使她受更深刻更苦楚的新的刑罰。
埃娥正在細嚼着靑靑的嫩草;無垠的蒼穹復罩在她的頭上,微風吹得身上涼爽而舒適。沒有一個別的生物。連甲蟲和蝴蝶都沒有在這裏飛翔徘徊,她暫時息下冤苦的重擔。
但突然,身上狠狠的被什麼蟲叮咬了一下;她把尾拂打着,拂打着,但驅不去這小蟲。麻癢,痛楚,她受不了。不象是蚊子,也不象是草叢裏的蟲類。不知什麼地方飛來。她跳躍,但也震不落這怪蟲。又被狠狠的叮咬幾口。癢痛之極!她奔跑,震盪,騰跳,設法要把這怪蟲拋下身去,落在後面。但這怪蟲彷彿生根在她身上似的,老叮着她,成了她的毛孔的一部,血肉的合體。卻又那樣的作怪,一刻不停的咬着,齧着,叮着。剛在頸部,又在肩上。她回過頭頸,要拿齒與舌去咬它,卷它,吞它,趕它,它卻又跑到背嵴上去了。尾毛狠狠的向嵴上拂打着,枉自打痛了她自己,這怪蟲又滑到腿上了。積伶鬼似的,黑影子似的老是跟隨着她,老是叮咬着她,晝夜不停,風雨不去,簡直是成了她自己的最擾苦的靈魂的自身。咬着,叮着,齧着,這怪蟲!
她騰跳,她奔逃,她顫動,她臥倒,她將背在地上擦磨,總是趕它不去,拋它不下。
那一陣陣的麻痛,酸癢,使她一刻不能安息,一刻沒有舒氣休憩的空兒;反視亞哥斯監視着的時候爲最快樂的過去的一夢。她不能睡,剛閤眼,又被叮醒了,又痛,又麻,又癢。她站立着,那麼樣的不安寧,尾拂不停的在驅打,沒有用。自己拋擲在地上,磙着,擦着,臥着,轉側着,沒有用。永遠是又癢,又麻,又痛!
激怒得她又發了狂,她喘息着,沒命的奔跑,奔山過澗,越嶺翻谷。遠遠的,遠遠的,不知向什麼地方奔跑而去。沒有目的,沒有思想,只是發狂的奔跑着,如具有千鈞之力,而身上永遠的是被叮,被咬,又麻,又痛,又癢,驅逐不去,拋落不下,那可怪的怪蟲兒!
不知什麼時候,她奔到了高加索山,史克薩峯之下,她望見了大海,如得了最後的救主似的,她想自投到峯下海里死去,她痛苦得什麼都忘記了,連報復之念也消滅得不見。
但被囚的柏洛米修士見到了這,雷似的喊叫道:
“埃娥,埃娥,停着,聽我的話!”
好久沒有聽到有什麼人呼喚她的名字了,這呼聲使她感得親切。她停在巖邊。是一位白髮的老人被釘鎖在這絕壁懸巖之上。但她不能回答他,只是吽吽的叫着,其意是要問他是誰,何以知道她。
柏洛米修士明白她的意思,繼續的說道:“我是預言者柏洛米修士,被殘酷的宙士所毒害的一個,正如你一樣。你所受的苦難,我都知道。但你不要灰心。神之族是終於要沒落的,代之而興的是偉大和平的人類。你的仇,將得報復,不僅是你,凡一切受難受害者們的仇,皆將得報復。天堂將粉碎的傾復了,宙士和其族將永遠的被掃出世界以外。‘正義’和‘運命’是這樣的指導着我們。你不要灰心。被壓迫者們將會大聯合起來的!前途是遠大,光明,快樂。也許我們見不到,但我們相信:這日子是不在遠!你到埃及去,在那裏,你的咒詛將終了,你將回復人身,爲人之妻,生子。而你的子孫也便是參與倒神運動的主力的一部。”
埃娥不能回答他,但眼中顯出希望的光。她又恢復了她的勇氣與信念。
她到了埃及,定居在那裏。當宙士的咒語效力消滅了的時候,果然成了人之妻與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