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是暴風雨將來的一個黃昏。
死灰色的天空,塗抹着一堆一縷的太陽的紅焰,那刺目的豬肝似的惡毒的顏色,使人看了便有些壓迫之感,至少是不舒服。
宙士,神與人的主宰,鬱郁的坐在他的寶座上;伏在座下的鷙鷹,時時在昂頭四向,彷彿只等待宙士的命令一下,就準備着要飛騰出去,捕捉什麼人與物。他手上的雷矢,在炎炎的發着白熱以上的火光,照耀得立在他左右的諸神都有些目眩頭脹,間或隆隆的發着雷聲,其聲悶而不揚,正足以表示其主人翁的蓄怒未發的心境。
一切都是沉悶,鬱怒。
火山口將爆裂的一剎那,暴風雨將降臨的前一刻。
等候着!未前有的沉默與等候!
神們都緊皺着雙眉,裝着和宙士同憂共苦。連嬌媚的愛神愛孚洛特蒂也喬作顰態,智慧神雅西娜的無變化的淡靑色的臉上卻若在深思。宙士不時的象發疑問似的望着她。她並不變動她的深思的姿態,也一聲兒不響,活象一尊無感情無知覚的墓前的翁仲,永遠沉默的對着西墜的夕陽。天上的鉄匠海泛斯托士,那位柔心腸的殘疾者,心裏正忐忑不寧,不忍看這幕活劇的進行,但又不敢離開,只能痛苦的等待着。
權威與勢力,那兩位助桀爲虐的神的奴,一對玩鉄的鑄象似的緊密的站在宙士寶座的左與右;他們倆喜悅的躍躍欲試其惡辣的手腕;他們知道這場面上免不了他們倆的上演。他們握緊了有力的鉄似的雙拳在等待着。
一切都是沉悶,鬱怒。
等候着!未前有的沉默與等候!
二
神的廳上開始騷動起來,竊竊的微語。神們都轉臉向外望。宙士抖擻着威風,更莊嚴的正坐着,暗地裏在尋思着怎樣開始發泄他的久已不能忍耐的悶怒。權威與勢力活動了他們的緊握着鉄似的雙拳一下。座下的神鷹拍拍它的雙翼。
遠遠的有兩個黑點,在飛着似的浮動着。
這兩個黑點,近,更近,正向神的寶座前面來。
是他們所期待的人物!
前面執着蛇杖的是神的使者合爾米士,後面跟着他而來的,啊,便是那位叛逆的取火者柏洛米修士。
神的廳上轉又沉默下來,沉默得連一移足,一伸手彷彿都會有聲響發出。
“別來無恙,”那位叛逆的柏洛米修士的丰姿並沒有什麼變動;山峯似的軀幹,忠懇而有神威的雙眼,表現着堅定的意志的帶着濃髭的嘴脣,鬢邊的斑白的頭髮,因思慮而微禿的頭顱,以及那雙多才多藝的巨手,全都不曾發生變化。
一見到他,期待着壯烈的,殘虐的表演的諸神們反都有些茫然自失;一縷“反省”與“同情”的遊絲似幻成千千萬萬的化身,各緊粘着諸神們的心頭,擺脫不開。
未之前有的悽淸的空氣,瀰漫了神的大廳。
神的使者合爾米士首先打破了這場淸寂,循例的交差似的說道:
“父宙士,您命我去呼喚前來的柏洛米修士,現在已經在您面前了;他一聽到您的命令便和我一同動身。”
人與神的主宰宙士似最早便鎮攝住他自己的權勢和自重,使他立即恢復了他的嚴肅與殘忍。他向侍立的權威和勢力瞬了一眼,他們正鉄棒似的筆立着待命;雙拳是緊握的伸出,臉部是那麼冷酷無表情,這增加了宙士的自覚的威嚴。
他緊皺着雙眉,望着忠厚而多智的柏洛米修士本想立即咆吼的痛罵,卻出於他自料以外,發出來的語聲是那麼無力而和緩。
“啊,你竟又在我的面前出現了,柏洛米修士,我的好朋友——不,現在你已自動的背叛我們而向下等的猥瑣的人類那裏求同盟,大約已不承認老朋友們了罷?你有理由說明爲什麼背叛我們而和人類爲友嗎?”
柏洛米修士山峯似的站在那裏,並不恐懼,也不傲慢;他誠懇的微笑着,並不曾說什麼。
他該說什麼呢?
長久的沉默。
“你,怎麼一聲不響?”
宙士大聲的開始咆吼,但一望着他的那麼誠懇忠厚的臉部,又失了發怒的勇氣。“你說,儘管無忌憚的說,爲什麼你要把神們所獨有的神祕,火,偸給了人類,使他們如今如此的跋扈?”
想到了偸火的事,宙士不禁氣往上衝。火是神們的獨得之祕,是神的權威的代表,它只能放光明於神之廳與室,它只能供神作種種的利用的工具。有了這火,便足以誇耀於下等的人類之前,足以爲他們永久的主宰而不虞其反抗;人們是在永久的齷齪卑污的生活中度過去的;那麼可憐,那麼無告,卻正是神們所願的;這樣的人類,卻恰好是最適宜的神之奴。宙士和諸神們從沒有想到這神祕的火會由神之天堂而移殖到人世間,而供猥瑣可憐的人類利用的。然而這火卻終於不能成爲神的獨有之祕密!
三
某一個冬夜,宙士帶着他的兒子合爾米士踏着瓊琚似的白雪而周行於大地上。手掌大小的雪片,在空中飄飛着,北風虎虎的在發威,把地上的一點一滴的水都凍結成冰塊。大地上什麼都在沉睡,什麼都已深深的躲藏着。宙士挺了挺偉健的巨軀,全身充滿着熱力,雪花到了他身的周圍的一丈左右便都已無聲的融化而落在地上了;北風對於他也是服從慣了的,只是服服貼貼的悄然從他背後熘過去。
他們倆幽靈似的在雪地上走着,以克服了一切目喜。
他們也許便是此夜的僅有的夜遊者。
“啊,”宙士以全肺部的氣力叫道,他是高興着。
大地幾乎要迥應着他的遊戲喊聲而打了一個寒噤。
一個奇蹟突然出現了。
遠遠的,有一星紅光在若明若暗的照耀着,映着白雪的大地,似乎格外來得鮮明。
是星光,難道?
鉛灰色的天空,重重疊疊的爲黑雲所籠罩,所包裹,一點蔚藍色的空隙都沒有,哪裏會有什麼星光穿透重雲而出現?
宙士以肘觸觸跟在他背後的合爾米士,悄聲的說道:
“看見了麼,你?”
“看見的,”合爾米士微笑的隨意答道。他想,也許是嬌媚的愛神又在進行什麼新的情戀,結婚神正爲她執着火把吧?也許是她的兒子,那位淘氣的丘比得在鬧什麼玄虛吧?也許是羊足的薩蒂爾們正在向林中仙女們追逐着吧?也許是酒神狄奧尼修士正率領着他的狂歡的一羣在外面浪遊吧?
宙士沒有他那麼輕心快意的疏忽,這位神與人的主宰者,是飽經憂懼與艱苦的,一點點的小事,都足以使他深思遠慮的焦念着,何況這不平常的突現的一星紅光。
這不平常的一星紅光使他有意想以外的嚴重的打擊。
他有一種說不出恐怖的預警。
他一聲不響的向那一星紅光走去。
啊,突變,啊,太不平常的突變!
走近了,那紅光竟不僅是一點星了,一點,兩點,三點,……乃至數不淸其點數,此明彼暗的竟似在那裏向雪白的大地爭妍鬥媚,又似乎有意的彼此爭向宙士和他的從者投射譏笑的眼風。
連合爾米士也漸漸的感覚到一種不平常的嚴重的空氣的壓迫了。
走近了,——最先走近的一星紅光,乃是從孤立於雪地上的一間草屋的窗中發出來。
這草屋對於神與人的主宰者宙士異常的生疏,刺目。
他想:“這東西什麼時候創建在大地上的呢?”
他們俯下身去,向窗中望着。更嚴重的一幕景象顯呈於眼前。
一盞神們所獨有的油燈,放出豆大的火焰,孤獨而高傲的投射紅光於全屋以及雪地上。
是誰把這盞燈從神之廳堂裏移送到這荒原上來呢?
啊,更嚴重的是,對這盞燈而坐的,並不是什麼神或薩蒂爾們或林中仙女們,卻是那麼猥瑣平凡的人類。這些猥瑣平凡的人類,當這冬夜向來是深藏在洞窟之中的。
是誰把這盞燈從神之廳堂裏偸給了猥瑣可憐的神之奴,人類的呢?
宙士不相信他自己的眼。他咬得銀牙作響,在發恨。
“非根究出這偸火的人來不成!誰敢大膽的把神的祕密泄露了?只要我能促住這賊啊!……至於這些猥瑣的人類,那卻容易想法子……”
他在轉着惡毒的念頭,呆對着窗內的那盞油燈望着。
一陣嬉笑聲,打斷了他的毒念。
父親在逗着週歲的孩子玩,對燈映出種種的手勢。孩子快樂得“吧,——吧——”的手舞足蹈的大叫着。另一個三歲的孩子伏在他媽的膝蓋頭,在靜靜的聽她講故事。
一陣鬨堂大笑,不知爲了什麼。
這笑聲如利刃似的刺入宙士的耳中,更增益了宙士的憤怒。
“這些神的奴,他們居然也會滿足的笑樂!住神所居的屋!使用着神的燈!而且……滿足,快樂!”
妒忌與自己權威的損傷,使得宙士痛苦。他渴想毀滅什麼;他要以毀滅來泄憤,來維持他的權威,來證明他的至高無上的能力。
勐一擡頭,一陣火光熊熊的高跳起,在五六十步的遠近處。
隨着聽到乒乒乓乓鉄與鉄的相擊聲。
“這是什麼?”他跳起來叫道。
他疑惑自己是仍在天上,正走到鉄匠海泛斯托士工作場,去吩咐他冶鑄什麼。
那鉄與鉄的相擊的弘壯的音樂,有絕大的力最,引誘他向前去。合爾米士默默的隨在後邊;他也是入了迷陣;卻不敢說什麼,他明白他父親,宙士,正蘊蓄着莫名的憤怒。
那是一個市鎮的東梢頭,向西望去,啊,啊,無窮盡的草屋,無窮盡的火光!
這鉄工場雄健的鎮壓在市的東梢頭,大敞着店門在工作着。火光烘烘的一陣陣的跳起;紅熱的軟鉄,放在砧上,乒乒乓乓的連續的一陣陣的重擊,便一陣陣的放射出絢爛的紅火花。那氣勢的弘偉壯麗,只有在海泛斯托士的工場裏纔可見到。然而如今是在人世間!
宙士和合爾米士隱身在鉄工場一家緊鄰的檐下,聚精會神的在望着那些打鉄的工人們。
鉄與鉄的相擊聲,此鳴彼應的,聽來總有五六對工人在鉄砧上工作,但他們只能見到最近的一對。
年輕的一對小夥子,異常結實的身體,雖在冬夜,卻敞袒着上身;臉色和上身,鉄般的黑。鉄屑飛濺在他們的手上,臂上,臉上。一個執着火鉗,鉗着一塊紅鉄放在砧上。他們掄起龐大的鉄錘來,一上一下的在打,在擊。紅熱的鉄花隨了砧錘聲而飛濺得很遠。兩臂的筋肉,一塊塊的隆起,鉄般的堅強。紅光中映見他們的臉部,是那麼樣的嚴肅,自尊與自信!這形相是神們所獨有的,而今也竟移殖到人世間!
火光映到兩三丈外的雪地,鮮紅得可愛。
火光半映在宙士的臉部,鉄靑而憂鬱。
天上?人間?
一個嚴重的神國傾危的預警,突現於他的心上。
瞬間的悽惋,憂鬱,又爲對於自己權威的失墜之損傷所代替。這傷痕,隨着砧與錘的一聲聲的相擊而創痛着。而望着那些自重的滿足的鉄工們的臉部,又象是一個新的攻擊。
他回過臉去。他狼狽到耍塞緊了雙耳。
那清朗,滿足,快樂的鉄與鉄的相擊聲,繼續的向他進攻,無痕跡的在他心上撕着,咬着,裂着,嚼着。
咬緊了牙,臉色鉄靑而鬱悶的轉了身,他向天空飛去。
合爾米士機械的跟隨着他。
四
這回憶刺痛了宙士的心的瘡痕。
“你有什麼可辯解的?”
宙士雷似的對柏洛米修士叫道。
“爲什麼一聲不響?”
他爲柏洛米修士安詳鎮定的態度所激怒;血盆似的大口,露出燦燦的白色牙齒,好象要把世界整個吞下去。手緊捏了雷矢一下,便連續的發出隆隆的雷聲,震得他自己也耳聾。
權威和勢力齊齊的發出一聲喊,山崩似的:
“說!”
他們的兩對鉄拳同時衝着柏洛米修士的臉上,晃了兩晃,腕臂上的靑筋,一根根的暴起。
柔心腸的鉄匠海泛斯托士,打了一個寒噤,回過臉去。
柏洛米修士卻安詳而鎮定的站在那裏,山嶽似的不動半步。
“爲什麼不說?”
宙士又咆吼着。
柏洛米修士銀鈴似的語聲在開始作響;那聲響,忠懇而清朗,鎮壓得全廳都靜肅無譁。
“你,宙士,要我說什麼呢?你責備我取了火給人類。不錯,這火是我給了他們的,我不否認。至於我爲什麼要幫助人類而和他們爲友呢?這,你也許比別人更明白:我從前爲什麼幫助了你和諸神們,我現在也便要以同樣的理由去幫助人類。”
這又刺傷了宙士,他皺着眉不聲不響。
“我當初覚得你和你兄弟們受你們父親的壓迫太甚,所以,爲了正義與自由,我幫助了你們兄弟,推翻了舊王朝。但自從你們兄弟們創建了新朝以後,你們的兇暴卻更甚於前。你父親克羅士是專制的,但他是個人的獨裁。你們這羣乳虎,所做卻是什麼事!去了一個吃人的,卻換了無數的吃人的;去了一位專制者,卻換來了無數更兇暴的專制者。你,宙士,尤爲暴中之暴,專制者中的專制者!你制服了幫助你的大地母親,你殘害了與你無仇的巨人種族,你喜怒無常的肆虐於神們,你無辜的殘跛了天眞的童子海泛斯托士;你蹂躪了多少的女神們,仙女們!你以你的力量自恣!倚傍着權威與勢力以殘橫加人而自喜!以他人的痛苦來滿足你的心上的殘忍的慾望!你這殘民以逞的暴主!你這無惡不作的神閥!你說我離開了你,不和你爲友,是的,你已不配成爲我的友;是的,我是離開了你!我爲了正義和自由而號呼,不得不離開你,正和我當初爲了正義和自由幫助了你一樣!”
他愈說愈激昂。斑白的須邊,有幾粒汗珠沁出,蒼老的雙頰,上了紅潮,脣邊有了白沫,面貌是那麼凜然不可侵犯,彷彿他也便是正義和自由的自身。
宙士默默的在聽着責罵,未之前聞的慷慨的責罵。在他硬化的良心上,這場當衆的責罵,引不起任何同感,卻反以這場當衆的責罵爲深恥。他的雙頰也漲紅了,雙眼圓睜着,手把雷矢握得更緊,——雷聲不斷的在響,彷彿代他回答,以權威回答正義的責罵——血嘴張得大大的,直似一隻要撲向前去捕捉狐兔的勐獸。
海泛斯托士驚得臉色發白,他知道有什麼事要發生。廳上的諸神們半聲兒也不敢響。
這嚴重的空氣從不曾在神廳上發生過。
五
柏洛米修士山嶽似的站立在那裏,安詳而鎮定;他等候最壞的結果,並不躲避。
宙士並沒有立時發作。
柏洛米修士又繼續的陳說:
“至於我爲什麼選擇了人類爲友呢?”
他望了望廳上的諸神,悲慼的說道:
“我要不客氣的說了:完全爲的是救可憐的人類出於你們的鉄腕之外。人類呻吟在你們這班專制魔王的暴虐之下,已經夠久了;你們佈置了寒暑的侵凌,秋冬的枯藁;水旱隨你們的喜怒而來臨,冷暖憑你們的支配而降生;乃至風霜雨露,草木禽獸,無不供你們的驅使,作爲你們遊戲生殺予奪的大權的表現。爲了你們的一怒,不曾使千里的沃土成爲赤地麼?爲了你們的厭惡,不曾在一夜之間,使大水飄沒了萬家麼?雅西娜不曾殺害無辜的女郎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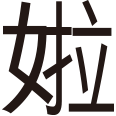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慶麼?她死後,不還把她變成蜘蛛,苦擾到今麼?日月二神不曾爲了他們母親的眥睚之怨而慘屠妮奧卜所生的十四個少男、少女麼?……你們這些專制的魔王們恣用着權威,蹂躪人類,剝奪了一切的幸福與生趣,全無理由,只爲了遊戲與自己的喜怒。這是應該的麼?啊,啊,你們的一部《神譜》,還不是一部蹂躪人權的血書麼?無能力的人類,除了對你們祈禱與乞憐,許願與求赦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趨避之途呢?而你們卻以濫用這生殺予奪的大權自喜。以人們可憐的慘酷的犧牲,作爲你們嬉笑歡樂之源!假如世界上有正義和公理這東西存在,還能容你們橫行到底麼!”
慶麼?她死後,不還把她變成蜘蛛,苦擾到今麼?日月二神不曾爲了他們母親的眥睚之怨而慘屠妮奧卜所生的十四個少男、少女麼?……你們這些專制的魔王們恣用着權威,蹂躪人類,剝奪了一切的幸福與生趣,全無理由,只爲了遊戲與自己的喜怒。這是應該的麼?啊,啊,你們的一部《神譜》,還不是一部蹂躪人權的血書麼?無能力的人類,除了對你們祈禱與乞憐,許願與求赦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趨避之途呢?而你們卻以濫用這生殺予奪的大權自喜。以人們可憐的慘酷的犧牲,作爲你們嬉笑歡樂之源!假如世界上有正義和公理這東西存在,還能容你們橫行到底麼!”他停頓了一卞,以手拭去額際的汗點。
“你們以爲人類便可以永久供你們奴使,永久供你們作爲尋求快樂的犧牲品麼?這形相不殊於你們,且有更光明的靈魂的人類,難道竟永久壓伏在你們專制之下麼?不,不,宙士,當你們神之宮裏舉杯歡宴,細樂鏗鏘的時候,你們知否人類是如何的在呼籲與憤怒!當你們稱心稱意在以可憐的被選擇的人們作爲歡樂的資料的時候,你們知否人類是如何的在詛咒與號泣!”
柏洛米修士睜大了雙眼,彷彿他自己也在詛咒,在憤怒。額的中央暴露一條條的靑筋,眼邊有些潮溼,語聲有些發啞,幾要爲着人類放聲哭一個痛快。
勉強鎮定了他自己,又陳說下去:
“這詛咒,這哭聲,達到了遼遠的我的住所;這哭聲,這詛咒,刻刻在刺傷我的良心。我爲了正義,爲了救人類,老實說,也爲自己良心的慰安,我不能不出來做點事。這便是我取了火,一切智慧、工藝的源泉,給了人類的原因。”
恢復了安詳而鎮定的常態,彷彿大雷雨之後的晴朗的靑天似的,柏洛米修士山嶽似的屹立在神廳中,等候着什麼事的來監。
石象似的諸神,呆立或呆坐在那廳上;海泛斯托士感動得要哭出來。愛神的嫩臉,羞得通紅,她也許正憶起了生平千件的不端的戀愛。雅西娜和月神亞特美絲恨得拖長了她們的靑臉,咬着牙想報復。
宙士頻頻冷笑着,望望左右立着的權威和勢力;他們倆象兩支鉄棒似的筆立着,磨拳擦掌的待要發作。
“你說完了話麼?我的好心腸的柏洛米修士!現在輪到我的班次了。我不說什麼。我要使你明白‘力量’勝過‘巧辯’。來,我的忠僕們!”
權威和勢力機械似的應聲而立在宙士的面前。
“把他釘在高加索山的史克薩尖峯上,永遠的不能解放,爲了他好心腸的偷盜。”
鉄匠海泛斯托士低了頭,兩條淚水象珠串脫了線似的落在地上。他爲仁愛喜助的柏洛米修士傷心。
宙士瞥見了這,又生一個惡念。
“而你,我的鉄匠,你去鑄打永遠不斷裂的鉄鏈,親自把柏洛米修士釘在那巖上。”
海泛斯托士不敢說什麼,低了頭走出廳去,詛咒他自己那可詛咒的工作。
六
權威和勢力各執着柏洛米修士的一臂向廳外拖。
“停着!”宙士又一轉念,叫道。
柏洛米修士的臂被放鬆了。他安詳而鎮定的象山嶽般的屹立着。
“爲了顧念到你從前對於我的有力的幫助,我給你以一個最後的補過的機會:把火從人類那裏奪回來,當人類被奪去火的時候,你的罪過也可被赦免。”
柏洛來修士不動情的屹立着,默默不言。
“怎麼?不言語?爲了猥瑣平凡的奴隸,人類,你竟甘心受罪麼?”
“不,奪回‘火’的事是不可能的了!我怎麼能夠‘出爾反爾’的賣友求免呢?這是一。再則,老實說,‘火’是永久要爲人類所保有的了。我去,你去,你們都去,都將奪不回來的了。這‘火’在每一個屋隅,在每一個工場,在每一個廚間;在每一個灰堆中,都堅頑的保有着。你們固能毀壞,奪回其一,其二;但你們能把每一個灰堆中的火種都奪去了麼?把每一屋裏的油燈都譭棄了麼?把每一件敲火器都拋到遠遠的所在去麼?不,這是不可能的了!火成爲深藏在每一個人心裏的知識的源泉。你能把每個人的心都奪去麼?火也便是知識的本身,其光明使人類照耀着正義與自由的自覚;你能把人類對於正義與自由的自覚都奪去麼?不,這是不可能的事了;——除非毀滅了整個的人類。”
“啊,啊,我便毀滅了整個的人類!”
宙士自負的冷笑道。
“這也是不可能的了。”
“爲什麼?我也不是曾經毀滅一次人類麼?”
“不,這次你是不可能毀滅他們的了。”
“爲什麼?”
“因爲他們已經得到了火,成爲不可克服的了!火使他們知道怎樣保護他們自己;怎樣爲了他們的自由與平等而爭鬥;火給他們以無量數的智慧,以無窮大的力量。他們將不再向你們這些神閥乞憐,祈禱的了!他們將不再在你們之前逃避,躲藏,求赦的了!他們也不再詛咒,不再哭泣的了!不,他們將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反抗。只要你們敢去和他們爭鬥,你們將見到他們新的力量的偉大與不可克服。他們將永不再受着你們的奴使與支配;他們要用他們自己的力量支配自己,爲自己同類而服役,一人爲全體而工作,而全體爲一人而存在!他們將永不再成爲你們娛樂的犧牲,喜怒不常的泄憤的對象;他們要用他們自己的力量來反抗外來的一切壓迫,不,他們的新的力量,還足夠撼動神之國的基礎的。”
“什麼!我將使你知道我的力量。巨人的一族都爲我所滅絕,何況猥瑣無力的人類。”
宙士氣沖沖的說道,但他開始有些氣餒,他知道預言者的柏洛米修士的允許是不會落空的。
“不,他們將不再感覚到你的力量的了;巨人族因愚蠢爲你們所滅。但人類卻將有一個遠比你們更偉大,更光明,更快樂的前途;他們對於‘火’的利用,將不是你們這班橫暴無智的神閥們所瞭解的。啊,你們只會把‘火’來照亮夜宴,來幽會,來裝飾神的廳與室,來鑄打兵器與鉄鎖,來作爲毀滅敵人的工具。但人類卻將‘火’的功用改變了;‘火’將不再是個人的裝飾品,將不再是神閥的工具,將不再是陰謀與個人主義的奴役。它幻變了千萬個式樣,爲全人類而服務,爲向全人類的光明、幸福的生活的創建之目的而服務。啊,‘火’,我終於見到你是向着最光榮,最正當的使命而服役的了!”
柏洛米修士微仰着頭,說教者似的,滔滔的陳說着,爲他自己的幻想所沉醉。
“什麼!你敢在我面前爲人類誇口!”宙士咆哮道。
“這是事實,宙士,你將會知道。”
“好,你等着,你看我將再在一夜之間把整個人類都掃蕩到地球以外。”
“不,宙士,不要逞強,這不是你力之所能及。”
“啊,啊,恰是我力之所能及的!”
“不,宙士,不要太自負了;人類已不復是猥瑣無力的人類了,從得了火之後,在極短的時間裏,他們已使他們自己具有了神以上的新的能力。”
“什麼,神以上的能力,你們聽聽,這不是瘋話!”
宙士向左右的諸神望望,諸神機械似的點點頭。
“我幾曾有過‘超事實’的允許!”預言者的柏洛米修士懸切的說道。
“隨你的意思去允許什麼吧,我是決意將要掃蕩那批猥瑣的人類的了。”
“你不能,宙士。”
“我能,柏洛米修士。”
“絕對的不能,我說。”
“絕對的能!我說。”
他們之間,幾乎是鬥嘴的姿態。
“當你們敢去和人類發生新的鬥爭的時候,宙士,被掃蕩出大地以外的將是你們而不是人類。”
柏洛米修士安詳而鎮定的預言道。
“什麼!你這暴徒!敢!”
宙士再也忍不住,大聲咆吼道,整個神之廳都爲之一震。
“來,把這叛逆帶到高加索山去!”
權威和勢力各執着柏洛米修士的一臂,向外推,形相猙獰得怕人。
“我因了幫助有偉大的前途的人類而受到苦難,我不以爲憾。柏洛米修士安詳而鎮定的回過頭對宙士說道。“但,宙士,你的權威的發揮,將以我的犧牲爲最後的了!”
“什麼!”
宙士的憤怒的水閘整個的拉開了;他忘其所以的,雙足重重的頓着,緊緊的把握着雷矢的那隻手,在桌上重重的擊了一下。一聲震天動地的霹靂,煙火和硫磺氣瀰漫了整個神之廳。愛神愛孚洛特蒂驚得暈倒了;丘比特大叫的藏在椅下。宙士他自己也被震得耳聾。神之後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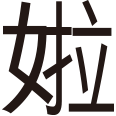 幽幽的哭了。雅西娜還是石象似的站立着。但她靑色的臉部卻籠罩上一層未之前有的殷憂之色。
幽幽的哭了。雅西娜還是石象似的站立着。但她靑色的臉部卻籠罩上一層未之前有的殷憂之色。雷聲不斷的大作,電光在閃,每一電鞭,都長長的經過半個天空。鉛灰色的天空,重重的爲破碎的綿絮似的雨雲所籠罩。大雨傾盆的倒下去。
大雷雨象永不停止似的在傾泄,彷彿在儘量的表演神閥的最後的威力。